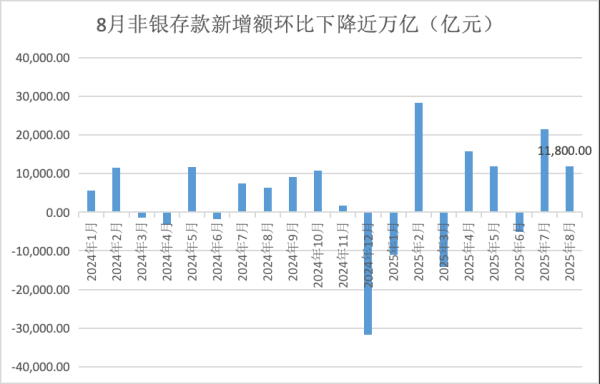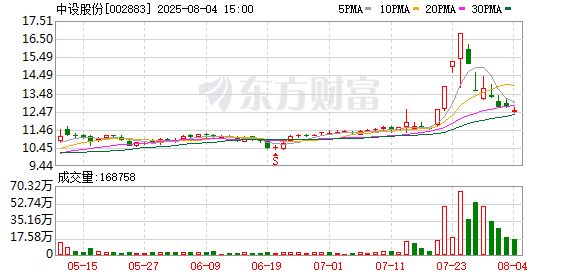阿富汗的崇山峻岭间,至今流传着关于“远方来客”的传说。当地牧民在兴都库什山脉放牧时,偶尔会捡到锈迹斑斑的方孔铜钱配资论坛推荐网,上面的汉字已模糊难辨。这些遗物默默诉说着一段被淡忘的历史:中国古代王朝曾不止一次将兵锋指向这片被称为“帝国坟场”的土地,其中最著名的,当属唐朝对吐火罗地区的经略。
唐朝初年,阿富汗所在的中亚地区被称为“吐火罗”,分布着大小数十个城邦国家。当时的吐火罗处于波斯、突厥与印度文明的夹缝中,各国为求自保,纷纷向强盛的唐朝遣使称臣。贞观年间,唐太宗设立安西都护府,将吐火罗纳入“羁縻府州”体系,册封当地首领为都督、刺史,看似不费一兵一卒便将影响力延伸至中亚。
这种和平局面在高宗时期被打破。公元667年,大食(阿拉伯帝国)势力东扩,攻陷吐火罗重镇缚喝(今阿富汗巴尔赫),当地王公向唐朝求援。唐高宗任命裴行俭为“安抚大食使”,率精兵万余西征。裴行俭利用熟悉西域地形的优势,在俱密国(今塔吉克斯坦境内)设伏,大败大食援军,一度收复缚喝城。此役后,唐朝在吐火罗设立月氏都督府,直接驻军镇守,这是中原王朝首次在阿富汗地区建立实质性统治。
展开剩余74%然而驻军的代价远超想象。兴都库什山脉的险峻地形,让粮草运输成了致命难题。从安西都护府治所龟兹(今新疆库车)到缚喝城,全程五千余里,需穿越沙漠与雪山,运粮队往往十去五不还。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,仅公元670年,唐朝为维持吐火罗驻军,便消耗了关中地区三年的粮草储备,百姓徭役负担陡增,民间怨声载道。
更棘手的是当地复杂的部族关系。吐火罗各国虽名义上臣服唐朝,却各有盘算。当大食势力卷土重来时,不少城邦暗中倒戈,甚至联合袭击唐军哨所。公元674年,唐朝派驻吐火罗的守将王方翼遭部族联军围困,苦战三月才突围而出,所部千人仅剩三百。这场败仗让唐朝意识到,单纯的军事压制难以奏效,不得不转为“以夷制夷”,扶持亲唐部族对抗大食。
武则天时期,对吐火罗的经略达到顶峰。公元694年,她任命阿罗憾为“波斯军使”,统领中亚各国联军,在吐火罗大败大食与吐蕃联军。此战过后,唐朝在吐火罗册封了16个都督府,将疆域名义上拓展至阿姆河流域。但这种“辉煌”背后,是每年数百万缗的军费投入——相当于当时唐朝全年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,成了沉重的财政包袱。
安史之乱成了唐朝退出中亚的转折点。公元755年,安禄山起兵反叛,唐朝将安西都护府的精锐调回平叛,吐火罗地区的防御瞬间空虚。大食趁机发动猛攻,当地唐朝驻军孤立无援,最终全部战死。公元768年,最后一座唐军戍堡被攻破,守将郭昕(郭子仪侄子)率残部战死,至此,唐朝在吐火罗的统治彻底终结,前后仅维持了约百年。
除唐朝外,元朝也曾与阿富汗地区发生过激烈碰撞。1219年,成吉思汗因花剌子模杀害蒙古商队,亲率大军西征,攻陷了当时属于花剌子模的阿富汗北部城市赫拉特。蒙古军队采用屠城威慑策略,赫拉特城破后,全城居民几乎被屠戮殆尽,这让阿富汗诸邦望风而降。但蒙古的统治同样短命,随着窝阔台去世,蒙古帝国内部分裂,阿富汗地区逐渐被帖木儿帝国取代。
对比汉唐与近代列强的阿富汗征战,会发现惊人的相似之处:地形险峻导致后勤困难,部族林立难以建立有效统治,外部势力(如大食、苏联)的持续介入,最终让入侵者难以为继。唐朝虽未像近代英国、苏联那样深陷战争泥潭,却也付出了巨大代价——据统计,唐朝在吐火罗地区的用兵,直接导致关中地区人口减少三成,间接加速了藩镇割据的形成。
值得一提的是,古代中国对阿富汗的经略,并非单纯的军事征服,更伴随着文化与经济交流。唐朝时期,吐火罗的佛教僧侣频繁前往长安,将梵文佛经译为汉文;中国的造纸术、丝绸技术也通过吐火罗传入阿拉伯世界。这种交流留下的印记,至今仍能在阿富汗的佛教遗址中找到——巴米扬大佛的壁画上,能看到明显的唐风服饰与绘画技法。
回望历史,中国古代王朝对阿富汗的征战,虽未像“帝国坟场”那样留下惨败的记录,却也证明了这片土地的难以驯服。唐朝的经验表明:武力或许能一时征服,却无法长久统治,唯有尊重当地文明与利益配资论坛推荐网,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共处。这或许正是那段历史留给我们的深层启示——在这片被群山环抱的土地上,从来没有永远的征服者,只有相互理解的可能。
发布于:四川省方正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